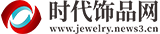95后女孩,和父母彻底决裂
何兰心很小就习惯了自己洗衣服,但小两岁的弟弟,“我妈给他洗了,还给他晾了。”平时饭后洗碗、拖地、倒垃圾等事宜,也由何兰心负责,“我大弟弟那时候23岁了,什么都不用做。”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断亲,意指亲属关系的终止或断绝。
近年来,这一概念逐渐被广泛讨论,但多数人所谓的“断亲”,只是断绝与亲属间的往来和联络。
而95后的何兰心,自小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。27岁那年,她经历了与家人“决裂”“断联”,最后被父母告上法庭、解除亲子关系。
有时,告别一段关系,并不等同于失去。
正如何兰心经历的那样,逃离原生家庭后,才抵达她想要的人生旷野。
仔细回想,何兰心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,仅仅因为两件不起眼的小事,她与父母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无法和解的“战争”。
那是2020年10月,晚饭时,何兰心和母亲坐在餐桌前吃饭。父亲回来后,挨着何兰心坐下,然后让她去拿一双筷子。
“我坐在中间,你自己拿不是更方便吗?”
何兰心拒绝了父亲的要求,最后母亲起身拿来了筷子。
饭桌上,父亲又提出让何兰心帮他洗牛仔裤,“用手洗,洗衣机洗不干净”,父亲强调。何兰心再次拒绝了。她吃完饭,慢步往房间走,听见父亲说了句“真懒”,何兰心随口答道,“我从小就懒,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。”
就在这时,母亲爆发了,她把筷子一摔,冲何兰心发火。何兰心也不示弱。她解释,并不是不乐意帮父亲洗裤子,如果能公平一点,让两个弟弟也稍微干点活,她就不会有怨言。
但从小到大,弟弟们没有被指使过做家务。
母亲无法理解她的想法,坚持认为她不该跟弟弟比,“以后还这样,就别回这个家了。”
在何兰心眼里,母亲向来强势,她不敢在母亲面前表现出不服气,顶嘴更是不可能。但那次,兴许是心里积攒的不满到了警戒值,何兰心立马撂下一句“不回来了”,就进屋收拾东西。
“最好别回来。”母亲最后向她喊。
夜很深,很冷。何兰心骑电瓶车驮着行李箱,边哭边赶路,身体一阵阵发抖。但天气再冷,也比不上心寒,50多分钟的车程中,何兰心逐渐意识到,自己在那个家“没有一点希望”。
“我就是得不到爱,应该停止去求爱。”她一路上跟自己讲,不要再有期待。
回到出租屋的何兰心,哭着拉黑了父母和弟弟的联系方式。
离家后,何兰心出国工作|讲述者供图
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残酷的一面给她看呢?
15岁那年,尚是读中学的年纪,何兰心收到一封母亲写给她的信,明确交待了她的身世,告诉她,大伯大妈才是她的亲生父母。看完后,何兰心觉得像做梦一样,每天上课也有些恍惚,她不敢相信,电视剧里的情节,居然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也是那时起,母亲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。
“很冰冷,对我爱搭不理”,“她就好像突然解脱了,扔掉了一个担子一样,不再管我任何事情了。”
她从前不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,偶尔和母亲争执,也会理直气壮地吵回去。之后的日子,何兰心再不敢那么放肆,“小心翼翼”成为她在那个家庭中的生存法则。
决意说出何兰心的身世,是母亲在释放“放弃”的信号。这一猜测很快被证实。升高中的那个暑假,何兰心突然从堂妹那里得知母亲怀孕的消息,“他们决定生一个亲女儿,问过我大弟弟后,就决定备孕。”
一年后,母亲和舅妈闲聊,何兰心也在场,母亲却毫不顾忌地说,她其实想生一个女儿,没想到还是生了个儿子。
亲耳听到这句话,何兰心觉得被家族抛弃,“完完全全不把我当人。”
她的性格开始往相反的方向发展。由以前的大大咧咧,逐渐变成老好人,“不自信,不太敢表达自己,甚至有点讨好型人格。”
上高中时,只要有同学需要帮助,何兰心就会施以援手,企图以主动付出的方式来获得关注,“因为打内心里觉得自己不配被爱,不配被尊重,认为这样才能让别人更喜欢我一点。”
自残的行为也有过。
得知身世后,何兰心每天放学都不愿回家。加之成绩也不好,她觉得人生陷入无望之中。那时,拿到任何尖锐的东西,她都习惯往胳膊上划,留下一道道的印记后,再用长袖遮起来,假装无事发生。
1995年,何兰心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。她原本是大伯大妈的第二个女儿,后来大妈再次怀孕,就把一岁的何兰心送到叔叔家暂养。没想到第三胎生下来还是女儿,大伯大妈决定将何兰心送人。
“到底是何家的血脉”,叔叔婶婶有些不忍,提议把何兰心过继到家里,成为她名义上的父母亲。一年之后,叔叔婶婶有了自己的儿子,加上何兰心,四口之家也算过得温馨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,何兰心逐渐展现出不同于家族姐妹的一面。堂姐堂妹全都乖巧、温顺,是她们父母眼中的“小棉袄”,只有何兰心“性子比较野”,喜欢到处疯跑。
父母是爱面子的人,管束自然也就多了起来。
何兰心上小学时,市里举办了一个舞台表演节目,报名者有上电视的机会。她从小喜欢唱歌,就想说服父母给自己报名,可惜和父亲大吵了一架,最后也没能参加,反倒成了父母口中“不听话、不懂事”的证据。
之后,但凡有违逆父母的行为,何兰心就会被打上“叛逆”的标签。直到15岁那年,倍感失望的母亲主动坦白了何兰心的身世,备孕下一胎。
他们不愿再在她身上倾注心血,来自家庭的束缚却没有减少。
大二那年,何兰心计划用自己攒下的钱去越南旅游,刚坐火车抵达南宁,消息就传到了父母那里。电话如轰炸般接连打进来。最终,迫于父母的压力,何兰心哭着回了学校。
受阻最大的一次,是她想要争取做美国互惠生(一种自发的青年活动,意在给世界各国青年提供一个在寄宿家庭里学习语言的机会)。
大伯大妈和舅舅得知后,全都找她谈话。
何兰心在美国做互惠生时,去阿拉斯加旅游|讲述者供图
“他们一觉得不安全,二觉得这个事情没意义。让我早点结婚,找个稳定的工作,趁年轻生孩子,不要跑来跑去到处瞎搞。”
劝说不下,家人又找来家族中颇有名望的叔叔,他苦口婆心劝了几个小时,并承诺,只要何兰心留在国内,就帮她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
这没能打动向往更大世界的女孩,2018年7月,何兰心如愿飞去了美国。
两年的互惠生经历,让何兰心见识到不一样的世界。
而她的成长环境里,“你是孩子,一辈子都得听家长的。家长想让你当老师或考公,你就得去考,不听就是不孝顺,不孝顺就要被所有人谴责。”
2020年,何兰心结束了在美国的生活,回到嘉兴,在一家教育机构做英语老师,每天骑着电瓶车上下班。
做英语老师时,和学生们的合照|讲述者供图
平静的生活被打破,源自一场车祸。一天,骑车上班的何兰心被汽车撞伤,她早就意识到家庭中资源分配的不公,这件事再次提醒了她。
“我爸开保时捷,100多万,我妈是30多万的沃尔沃,我弟弟开宝马,也是三四十万,我那辆电瓶车2000多块钱,一直没有人觉得有任何问题。”至于房产,家里有5套,“弟弟高中毕业后,就有一套房子写到他名下。”
父母养育何兰心的方式,也和养育弟弟完全不同。母亲是很传统的女性,“认为女人就应该在家,负责做家务,男人负责在外面赚钱养家。”
因此,何兰心很小就习惯了自己洗衣服,但小自己两岁的弟弟,“我妈给他洗了,还给他晾了。”
平时饭后洗碗、拖地、倒垃圾等事宜,也由何兰心负责,“我大弟弟那时候23岁了,什么都不用做。”
种种区别对待,让何兰心想要“反抗”的心蠢蠢欲动,而后,因为“拿筷子”“洗裤子”两件小事,与父母的关系彻底崩盘。
那次离家后,曾有亲戚传话,让她“回家服个软”,她还是拒绝了。
尽管也会难过,但她清楚,这是一个逃离原生家庭的绝好机会,也笃信“决裂”只是时间问题,“我不后悔当时的决定。”
离家两年,何兰心和父母始终处于断联状态。
寻常日子还好,逢年过节,她也会期待在电话铃声响起时,能看到熟悉的号码。遗憾的是,这只存在于想象中。
何兰心逐渐适应了出租屋里的独居生活,每天看书、运动、追剧,偶尔逗逗养的两只小狗。
有一年,临近生日,何兰心在网上刷到一个两岁女孩过生日的视频,全家人围在女孩身边唱生日歌,那个场景一下子击中了她。
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哭,哭了一会儿才明白,因为我没有像她那样,得到过像视频里其他人的那种爱。”
那两年,何兰心内心深处始终抱有期待,希望父母没有彻底抛弃自己。尽管她离家没多久,他们就托人把她的物品送了过来,从此再无交集。
2022年夏天,何兰心申请新西兰的打工度假签证,填写申报材料时,需要父母的个人信息和她本人的户口本复印件。这给了何兰心一个主动联络父母的机会。
在新西兰,一只鹦鹉落在胳膊上|讲述者供图
“我其实是有一丢丢窃喜的,终于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让我不得不去找他们了,我还是会想要再见他们。”
她先给母亲打了个电话。因为换了新号码,母亲不知道来电人是谁。
听出她的声音,对面只说了句“你打电话干什么”就挂断了。何兰心再打过去,已经处于被拉黑的状态。父亲也一样,得知是她,电话里只有长久地沉默,之后传来了挂断的嘟嘟声。
联系不上人,何兰心去找了大伯大妈,也就是亲生父母。她想拜托他们约个地点,好和父母见个面。
听说她要去新西兰,大妈语气不善地质问,“为什么老是要折腾?为什么不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一点?”吵到激动处,她扇了何兰心耳光,并抄起手边的物件往她身上砸。
何兰心也很委屈,“你们生了我就把我送人,没对我负责过什么,现在还要打我?”她从地上捡起大妈扔来的东西,一一扔了回去。大伯在中间拉架,何兰心把肩上的背包狠狠砸到他身上。
接下来,何兰心被赶出了门。
带着“干架”后的亢奋,她将刚刚发生的一切讲给朋友听,“他们抛弃了我,还想继续打压我,对我的人生进行指责……我没有再可怜巴巴乞求爱和帮助。”
与大伯大妈对抗后,何兰心觉得一个全新的自己已然诞生,“这种为自己抗争的感觉太爽了,太畅快了。”
趁着气势,她连夜去找了父母。门铃摁响之后,母亲出来堵在了门口,“你来干什么?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。”
尽管两年没见,何兰心面对母亲时仍然会发怵。
她鼓足勇气进行交涉,母亲却以扰民为由报了警。调解无果后,母亲通过其他亲戚转告何兰心,要想拿到那些文件,就得同意把户口从家里迁出去。
“一般来说,收养的孩子,只要去民政局调解就能解除收养关系,但他们收养我的时候没有走正常流程,所以唯一的办法是,他们去法院告我,我同意调解后才能解除。”
2022年9月29日下午,何兰心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。
几天之后,三个人在法院见到最后一面。往日里争执不休的双方,那天出奇平静。母亲甚至向她送上了祝福,“她祝我未来去新西兰或者去闯荡世界一切平安。”
何兰心心里明白,父母之所以能如此平静,是因为再也不用再担心她会分走他们留给儿子的财产,“他们得到了想要的结果,我也自由了。”
迁入集体户口的第二天,何兰心成功抵达新西兰。
在新西兰那段时间,何兰心比以前耐心多了。
没了家人,她开始给自己当母亲,“我希望有一个怎样的妈妈,就怎样对自己。”
打工之初,由于很久没开车,对车辆不熟悉,开到一半后,车突然没电,她只好停在路边。她的第一反应是指责自己。等到冷静下来,又以妈妈的口吻安慰自己道,“没关系,刚到新环境需要适应,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”
她温柔地对待自己,但也保留了一定的攻击性。似乎只有这样,才能给予自己更好的保护。
在街上赶路,前边电瓶车上的男人随意吐口水,飘到她身上,何兰心拦住对方不依不饶,直到对方道歉为止。乘电梯时,碰到抽烟的男人,她会主动提醒对方,不能在公共场合抽烟。
脱离原生家庭后,何兰心找回了幼年的自己,重新快乐起来。
朋友灿灿见证了何兰心这几年的变化。
她们是从网上熟络起来的。第一次刷到何兰心的视频时,灿灿对她“没有很高的好感度”,彼时,何兰心更新的还“都是和男朋友的打打闹闹,以及生活日常”。
变化发生在何兰心回国之后。
一天,灿灿无意中发现何兰心点赞了许多与女性权益相关的帖子,“沉溺恋情的人怎么会关注这些内容?”这引发了灿灿的好奇。她留意了一段时间,发现何兰心不仅点赞,还会转发。
后来加上微信,两人发现彼此是“同一类人”,关系就越来越近。
天气晴朗,何兰心和朋友们出游|讲述者供图
2021年7月,何兰心顶着同事、老板的异样眼光,剃了个光头。现在,她出门从不化妆,也不穿裙子和高跟鞋,接受自己作为自然人的状态,“以自己的身体舒服感受为主。”
最近几年,结婚生育也从人生规划里剔除。
和家里断联后,她断断续续看了不少女性相关的书籍,阅读逐渐帮她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婚育观和人生观。
“好像许多男性结了婚,就多了个免费保姆”,而她不愿做“服侍别人的家庭主妇”。
何兰心承认,她很喜欢孩子,但此前养狗的经历让她意识到,自己并不适合做母亲,“我脾气非常暴躁,有时小狗犯了错会打它,虽然每次打完会后悔,但下次类似的事还是会发生。”
不考虑婚姻,她有大把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前些日子,何兰心结束了新西兰打工之旅,目前,她已经前往东南亚各国旅行。澳洲的打工签证也已经办下来,“9月份飞过去,可以在澳洲待两年。”
和小动物合照|讲述者供图
她未来的计划之一,是继续攒钱游荡世界,“也算完成我的环球梦了。”
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,何兰心从没停止过成长。她相信未来还有更大的世界等着她,“达成自己的一些目标和计划后,我希望把时间留给为女性和儿童争取更多的权益上。”
(灿灿为化名。)
出品丨如是生活
编辑丨桑桑
作者丨梁九京